11月26日晚,中国通史系列讲座“星期四晚上”第七讲在四十四号楼一层报告厅成功举办。本次系列讲座由中国传媒大学通识教育中心主办,为期两个月,共八场。
本次讲座由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党宝海主讲,聚焦于明清时期的历史。中国历代帝王中出身最贫寒的皇帝,他的治国方略是怎样的?明朝在16世纪的世界历史发展进程中处于什么样的位置?清朝的正统性如何确立?其满汉关系又如何处理?让我们一起来寻找答案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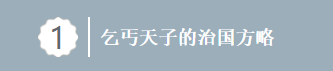
作为在元末群雄中脱颖而出,重建一统的帝王,朱元璋出身寒微之至。朱元璋是濠州钟离(今安徽凤阳东北)人,出身贫苦,父母和长兄皆死于疾疫。为生活所迫,朱元璋出家为僧,游方乞讨。早年的乞讨经历使他对底层社会的了解十分深刻,元末爆发的农民起义又给“小和尚”带来了巨大的转机。至正十二年,朱元璋投奔濠州红巾军郭子兴部,逐渐成为郭部将领,后渡长江向南发展。至正二十八年正月,朱元璋在应天府称帝,国号“大明”。闰七月,明军攻入大都,元朝亡。政权建立后,朱元璋进一步扩展疆土,将元朝的大部分疆土纳入版图。
经历元朝末年的大乱,朱元璋认为应该严格强化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于是制定了一系列加强社会管控的政策。
首先是户籍制。明初在全国进行了非常严密的户籍清查,在调查的基础上推行户计制,把全国的人口分成民户、军户、匠户等,分类管理,各立籍册。户籍一旦佥定,世代相袭,不得脱籍。对脱籍者穷究勾追,依律问罪,仍令复业。
其次是里甲制。每110户设为一“里”(城中称坊,近城称厢),推举丁、粮多者10户为“里长”,其余100户分为十“甲”,每“甲”又以一户任“甲首”。里长、甲首皆轮流担任,十年轮换一遍,负责管束所属人户,统计丁、产变化,督促生产,调解纠纷。如有强劫盗贼、逃军、逃囚、生事恶人,负责会集里人将其擒拿送官,违者加罪。
除了用里甲制将人丁管理到具体的单位之外,明初还施行了一系列教化措施。如在基层建立申明亭、旌善亭,张贴榜文,分别书善人善事﹑恶人恶事﹐以示惩劝。严惩毁坏亭舍、涂抹榜文者。推选年高德众的“老人”向里民宣讲法律、圣谕,使民知法畏法,各守本分。通过软硬兼施的奖惩制度对基层社区进行教化。
里甲制的实施将整个社会统一为一种有机的体系,又在社区中对居民严加管控。军民人等出行若超过百里,要向官府申请路引。又在州县关津要害之处设立巡检司,稽查往来行人,核验路引,限制了整个社会的流动性。严治“旷夫”、“逸夫”,强迫所有居民从事生产活动。“其有不事生业而游惰者及舍匿他境游民者,皆迁之远方。”对于乡里的富民大户,或谕告,或强迫其迁离家乡,甚至愤而杀之。胡蓝党狱“犯者不问实与不实,必死而覆其家。当是时,浙东西巨室故家,多以罪倾其宗。”
由卫所制度编排在一起的军士另立户籍,称军户。用强制手段征调民户为军。父子、兄弟相继,世代为军,非奉皇帝特恩不得更换脱免。军户必须有一人在指定卫所服役,称正军,其子弟称余丁或军余。正军应役,携妻及一名余丁同去。正军死亡,即以余丁替代,如家中已无余丁,则勾取其族人顶丁。军户的主要功能有屯田和守御,既解决了粮食问题,又解决了戍边问题。
对于官僚集团,朱元璋也采取了严惩苛治的态度,使用各种严刑峻法惩办贪污、渎职的官吏,对罪行严重者甚至用剥皮实草等酷刑。著名的洪武四大案——空印案、胡惟庸案、郭桓案、蓝玉案即是在整顿官吏、惩治贪污的过程中发生的四大事件,死者数万,对整个官僚集团产生了巨大的冲击。
在人才培养方面,朱元璋设立国子学,后改名国子监,广泛选拔品官子弟、民间俊秀通文义者入学。在府、州、县也广设学校,择优者入国子学。至洪武二十六年,监生数达8124名。且对监生待遇较优,时有赏赐,完成学业、考试积分及格者可直接任官;才学超异者,也可以奏请皇帝破格授职。但其学规严厉,对学生思想禁锢极为严重,强迫士人出仕,认为“寰中士夫不为君用,是外其教者,诛其身而没其家,不为之过”。
《大诰》是洪武中后期明太祖亲撰、刊布的刑事法规,实质上是一部案例汇编,辅以明太祖的训辞,集重刑恫吓与宣传说教于一体。内有处凌迟、枭首、族诛刑者千余,弃市以下刑者上万,绝大多数酷刑超出《大明律》的量刑标准。
朱元璋施行分封制,分封诸子为王,认为“如朝无正臣,内有奸恶”,则诸王可以帮助天子维持明朝的统治。建文元年(1399),燕王朱棣却利用此条法,以诛朝中“奸臣” 为名起兵,自称“靖难”。朱棣即位后,继续实行削藩政策,实则改变了朱元璋确立的“祖宗之法”。
在宦官问题上,明太祖禁宦官干政,而成祖却倚重宦官,充当耳目,放手使用。形成了具有十二监、四司、八局的宦官机构——“二十四衙门”。明英宗时期甚至出现了宦官专权的局面。
洪武十三年,朱元璋杀中书左丞相胡惟庸,废中书省,不设宰相,由皇帝直接统领六部。并且规定“以后子孙做皇帝时,并不许立丞相,臣下敢有奏请设立者,文武群臣即时劾奏,将犯人凌迟,全家处死”。在地方设立都、布、按“三司”。在军政方面也实行分权制,设立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分权。重视监察,设立督察院,创制“六科”,对六部进行行政监督。设置“检校”、锦衣卫等特务和特务机构。这些朱元璋创立的祖宗之法,为后人所延续,对整个明朝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建立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笼罩了整个明代,虽然一些制度随着社会发展而有所变化,但“祖制”的地位不容低估,是我们认识明代政治的一个最关键的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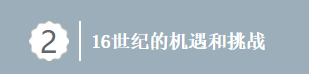
明中叶,即整个16世纪的发展,呈现出机遇和挑战并存的特点。在经济领域,商品经济迅速发展。江南等经济发达地区,多种经营兴盛。经济作物种植广泛,产品大量流入市场。出现了专业化市镇,如棉织业为主的松江朱泾镇、以丝织业为主的苏州盛泽镇、湖州南浔镇等。在一些地区农产品主要面向市场,粮食商品化,经营地主出现。商业性农业增加了全国各地的商业联系,出现了大宗货物市场,如粮食、棉花、棉布等。
在手工业领域出现了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即雇佣劳动、较大规模工场式生产。后期南方榨油、制瓷、矿冶、造纸等行业也零星出现。
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不变质、易分割、价值高的白银作为正式货币在市场上流通,白银的货币化又进一步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然而这种经济的发展却遭到了明政府滞后的管理观念的约束。嘉靖年间,蒙古部落土默特部的首领俺答汗要求与明互市,遭到拒绝。嘉靖二十九年,俺答汗对明朝发起大规模进攻,在北京城下大掠数日,继续要求互市,嘉靖皇帝依旧不予理睬。俺答汗“且犯且求开市”,致使明将战死十余人,北京城多次戒严。最终在穆宗隆庆五年与蒙古达成和议,结束敌对状态,明北部的边防压力才得以缓解。
国内贸易日益发展,沿海地主、富民从贸易中获利,海外贸易需求强烈,而明初以来却严格实行海禁政策,于是出现了大规模的海上走私集团。到隆庆时期开始解除海禁,有条件地允许私人从事海外贸易。隆庆、万历年间,福建、广东等地私人海外贸易才大大发展。
无论是陆地还是海洋,国家对商品经济的发展持约束和限制的态度。总体方针重农抑商,对商业活动课重税,严管理。明朝的闭关锁国政策也严重阻碍了对外贸易的扩大和海外市场的开拓。出于市场需求、以自由雇佣关系为基础的规模化生产,只出现于局部范围、局部行业,未成为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导向。对内皇帝与民争利,热衷敛财;对外又有边疆危机,东北建州女真逐渐崛起。在这种环境之下,商品经济未能对传统自然经济结构形成根本上的冲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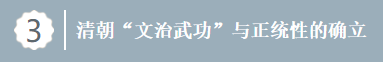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攻占北京,明朝名存实亡。清人认为入主中原的时机已经来临,于是调整战略,要为明朝“复仇”、“吊民伐罪”,整肃军纪,安抚地方,争取明士大夫和百姓的支持。崇祯十七年五月,清军进入北京,下令安辑百姓,为明思宗发丧。宣布明朝官员皆照旧录用,曾投降大顺者亦既往不咎。十月,顺治帝在北京祭天登基,颁诏天下,正式建立全国性政权。
顺治二年六月,占南京后一个月,清朝开始推行强制性民族同化措施,勒令全体汉族居民依照满族习俗剃发蓄辫,改易服饰,严重伤害了汉人的民族自尊心。各地出现骚动,很多已经降清的地方重举义旗,不同阶层广泛卷入反剃发斗争。在清朝严厉的血腥镇压下,反剃发斗争最终失败。此时民族矛盾激烈,满汉关系也极为恶劣。
因此顺治年间进行了政策调整,施行“文治”。宣扬“满汉官民,俱为一家”,进行大规模的免税,改革赋税征收制度。康、雍、乾三帝自幼接受良好的教育,具备很高的汉文化素养,甚至超出历史上绝大多数汉族皇帝。康熙帝在曲阜祭孔,在南京祭明孝陵,以儒家文化和明朝王统的继承者自居,使得汉族反清复明的诉求无所适从。标榜“崇儒重道”,优礼顺从的士人。康熙、乾隆多次到江南巡视,召见名流学者并赐官。或临时对当地士子进行考试,中者授官。对少量坚持“守节”、拒不出山者,也未过分逼迫。在种种政策的施行下,汉人的反清情绪大为缓和。
为了粉饰文治,清统治者频繁组织儒臣,开设书局,大规模修书。另一方面又施行文化专制,对思想文化界控制严密,多次兴文字狱屠戮士人。对书籍严格检察、禁毁,使得大批重要文献湮没无闻或残缺不全。
在军事方面,清朝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平定三藩;收复台湾;经过两次雅克萨之战和《尼布楚条约》的签订划清了东北的边界;并用康熙、雍正、乾隆三朝之力解决了和蒙古准噶尔部的斗争。
清统治者将这些赫赫战功刻石为碑,立于太学和孔庙。利用从中央到地方的孔庙与官学二元一体的教育体制,向全体汉族士人讲述新的帝国疆域与民族构成,构建新的政治与文化认同。通过这些举措,许多知识分子和民间的平头百姓也承认了清朝的正统地位,清朝的“正统性”最终在乾隆年间基本确立完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