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许珂 2019级新闻学本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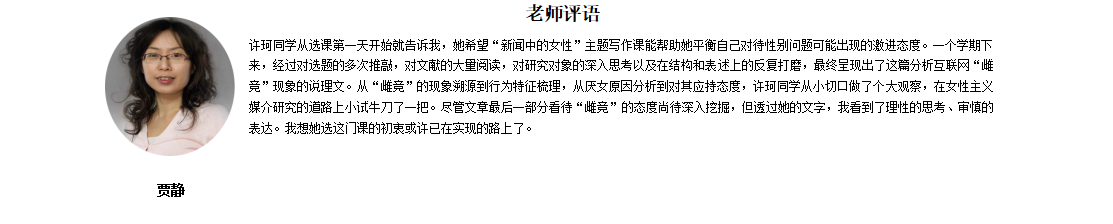
摘要:本文以当下广受关注的女性群体内部的“雌竞”(Pick Me Girl)现象为例,分析隐藏在其行为背后的内在动因和厌女逻辑。“雌竞”(Pick Me Girl)是指“在男性地位普遍较高的人类社会中,女性们争夺父权以及男权恩宠、并站在父权视角凝视并要求其他女性的现象”,本质是男权社会视角下女性主体意识不足的一种体现。本文通过网络参与式观察发现,在互联网时代,社交平台中出现的“雌竞”现象不仅受到媒介技术环境和社会结构因素的影响,其背后还存在深层的群体内部的女性嫌恶和厌女逻辑。即使新媒体赋权的理念已经被大众广为接受,但是如今女性自身的主体及性别意识仍处于薄弱状态,女性话语权还有待进一步加强。
关键词:厌女;互联网;雌竞
前言
伴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各类社交平台不断涌现,人们可以通过在此类平台发表意见并构建自己的互联网形象、实现观点共享。互联网的开放生态和连接一切的特性为用户创造了开放的讨论环境,并不断重塑出新的公共话语空间。
女性在适应媒介新型变化的过程中积极展现自己,并通过对刻板印象、女性污名化行为的一次次强有力的反击不断地提升着自己的网络话语权。
然而近些年,伴随着用户对互联网社交平台使用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很容易发现在女性群体内部出现了一种“贬低同性以吸引异性关注”的突出现象。女性用户在视频、图片、问题等多种形式的动态中试图传达“我比其他女人更好,所以pick me”的信号,这类出现在女性间的为迎合男性喜好而彼此贬低的现象被称为“雌竞”。
此前学术界已有许多学者都研究过与厌女现象相关的问题,景欣悦就在其文章中提到“‘厌女’不仅是一种文化态度或实践行动,而且兼具社会、历史、文本、意识形态等多种表现形式”1。而徐智与高山两位学者则在其论文中介绍了性别议题的网络表达与厌女症的相关研究成果,其认为“此前有关新媒体与性别相关的大多数研究都高度肯定了互联网的赋权意义”,但在另一方面,却“鲜少有研究专门讨论新媒体平台上的性别歧视和性别语言暴力等问题”。2
受此现象启发,本文试图以社交平台上的“雌竞”现象为例,解决以下几个问题:“雌竞”现象因何出现,又意味着什么?互联网在其形成过程中起到何种作用?互联网语境中的厌女行为展现出怎样的特征?我们又应当如何看待?
一、“雌竞”现象溯源
互联网中常出现的“雌竞”一词指“雌性竞争”,其对应于“雄性竞争”而存在,为了充分理解其内涵,我们可以借鉴生物学领域的性别选择理论以及贝特曼原理。
性别选择理论最早可追溯到达尔文时期,在1871年,达尔文提出了性选择学说,他认为雄性和雌性的繁殖社会行为不一样。雄性用廉价的精子使尽可能多的雌性受精;而雌性只有有限的大个的卵子,所以需要“选择”遗传质量最高的雄性来赋予后代上等的能力。
贝特曼原理是以英国遗传学家安格斯·约翰·贝特曼命名的,在生物学中,贝特曼原理指的是雌性通常在生育后代时投入比雄性更多的能量,因此在多数物种中雌性是有限的资源,雄性将为争夺它们而竞争。
从生物学角度来看,两性之间最显著的差异在于亲代投资不同。一般说来,雌性由于有更多的亲代投资,获取资源的时间又很有限,因此,在任一特定的时间内,有性接受能力的雌性会少于等待着交配的雄性。这引起了雄性之间的争偶竞争,也给雌性个体主动选择雄性个体提供了机会。所以自然界中的一般模型总是“雄性争偶、雌性选择”,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就被称为性选择。
生物学中的“雄性竞争、雌性选择”在人类社会中却发生了角色转换,这主要是由人类在漫长的社会演变过程中所形成的两性地位差异所造成的。
人类在征服自然的过程中形成了群居生存模式,伴随着群居生存模式的日益成熟又进一步出现了家庭及社会分工,而这些分工以两性间先天的体力差异为划分标准,进一步造就了人类社会“男尊女卑”的性别理念。在人类社会中,男性拥有更高的地位和更充裕的社会资源,女性只得通过“雌竞”的方式依附于男性来拓展自己的生存空间。
上野千鹤子曾在其《厌女》一书中提到“女人的厌女症”。其认为女人的厌女症表现为“自我厌恶”,因此女性通常试图利用“例外”策略将自己从女性群体中剥离,通过将其他女人看作自己以外的“他者”的方式来将这种厌女症转嫁出去。上野千鹤子在书中以作家林真理子为例,以其作品为例讲述了女人间的竞争,即本文所阐述的“雌竞”现象,并进一步将“雌竞”定义为“围绕女人的归属即‘被男人选上’而展开的斗争”。3
综上,我们可以将“雌竞”现象定义为“在男性地位普遍较高的人类社会中,女性们争夺父权以及男权恩宠、并站在父权视角凝视并要求其他女性的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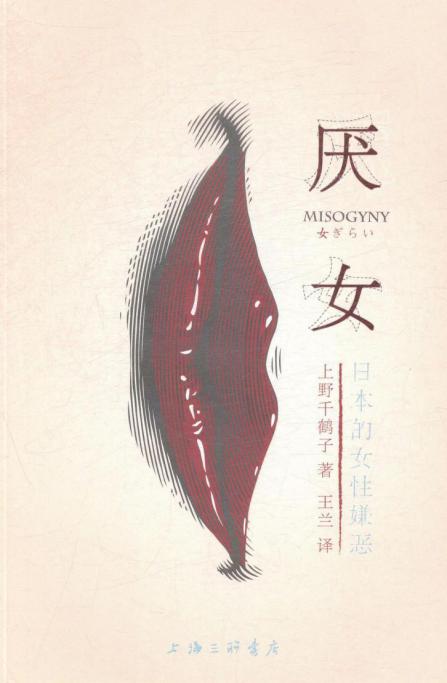
图1 《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
二、“雌竞”行为特征分析
当然,“雌竞”行为并非是互联网时代的新兴产物,但互联网却为其大范围传播提供了土壤。2018年,推特上出现了一个名为“#tweetlikeapickme”的话题,该话题自出现后就一路升温并迅速在各大社交平台走红,“Pick me”于是成为一种网络迷因,获得了更大范围的传播甚至模仿。而在中国,“雌竞”一词最早则是在微博平台由“@杨冰阳Ayawawa”等情感博主所带热的名词。直到2021年4月,微博用户关于“女性化妆是不是雌竞”话题的热烈讨论又进一步将这个现象呈现在大众面前。
在对互联网“雌竞”现象(Pick me girl)进行深入观察后,我们可以总结出此类行为的以下几个共性特点:
(一)在实现自我“例外”的同时,贬低其他女性。
在“雌竞”话语中通常会出现这样的表达:“我不喜欢和女生们玩,她们戏太多了。”这类特征印证了上野千鹤子在《厌女》一书中提到的“女人的厌女症”的特征。
即便是同样身为女性,女性的自我意识和接纳程度也并不是天然一致的,对自我性别的厌恶会使其通过不同的话语表达实现自我剥离。在自己与“其他女人”之间划定界限,使自己跳脱于“女性”定义之外,一方面可能是难以融入其他女性而不得不采取的自我保护手段,但如果在论证自己的“独特性”的同时还要借机贬低其他女性,这就属于“雌竞”行为。
(二)专注男女恋爱领域,努力迎合“贤妻良母”的刻板印象,甚至以此要求其他女性。
通常情况下,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的表现相对温和,其往往会将在恋爱关系中的“被拒绝”归因于自身,从而进一步聚焦于女性群体的内部竞争。
在当代女性追求经济独立与恋爱关系平等的社会浪潮中,“雌竞”行为似乎与之逆行。“Pick me girl”将其讨论的话题专注在两性关系领域,过度强调恋爱关系的重要性,甚至以此作为重点追逐的人生目标。“现在还是有女人什么都不图男人的,不图钱,不图物质,什么都不图,只想要信任、爱和惊天动地的激情。我就是她,她就是我。”的表达正是“雌竞”现象的突出案例。
以“有了女朋友,男人就不用洗碗、做饭、洗衣服了”为代表的这类“雌竞”话语重新强调传统的“娶妻当娶贤”的价值取向,进一步将女性的性别角色固化,将女性价值重新从职场、社会拽回到家庭中、灶台上,是当代性别意识发展过程中的一种明显退步。
“雌竞”将女性在家庭中扮演的“贤惠”形象看作其人格组成中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部分,将女性生活的重心完全放置在男性身上,并试图用一些僵化腐朽的“指标”将女性做二元区分,并以此作为评判一个女性“是不是好女人”的标准。其令女性在两性关系中甚至承担母亲角色,而男性则成为“婴孩”,似乎只要女性牺牲自我的个性和独立品质就能换来男性的青睐,将两性关系简单化、机械化,甚至庸俗化。
(三)立于男性立场与其共情。
在与女性“割席”的同时,“雌竞”行为还乐于以个体身份代表群体发言,其往往表现出强烈的反女权主义倾向,不仅要与女性“割席”,还要为男性“伸张正义”。
社交平台上经常出现这样的话语,“和女权主义者同为女性,我很抱歉”,甚至还有许多女性以受害者有罪论和性暴力等相关话题输出观点,其以女性身份替男性发言以博取关注。部分女性为达成吸引男性关注的目标,只顾盲目地表达关于性别问题的敏感观点,并试图通过所谓“换位思考”展现自己的理性立场。
这样的行为完全罔顾女性在现实社会中所处的真实环境,实际上不利于社会性别意识的良性发展和争取女性权利的斗争。
三、互联网中“雌竞”现象出现的原因
尽管“雌竞”现象在人类社会中长期存在,但互联网社交平台的出现为其搭建了一个更加直观生动的舞台。这类女性群体内部的“互相贬低以取悦男性”的现象当然并非仅仅存在于网络,同时更是一种现实的映射。
“雌竞”现象因何发生,互联网又对其出现发挥何种作用?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层面来思考:
(一)男性主导社会下不可避免的性别歧视
原始社会末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进入新的阶段,男性在主要的社会生产部门中逐渐占据主导地位。经济基础不可避免地影响到社会的上层建筑,于是,男性依靠经济上的优势,在社会生产和生活中也占据统治地位,父系社会由此形成。
英国人类学家梅因指出:在现代法律制度化之前,社会是由家庭构成的,而家庭本质上普遍是父权制的。“在家庭当中,年龄最大的男性家长,也就是最老的长者,是至高无上的。他的统治扩展到了生与死,无条件地加在他的孩子和家人身上,就像加在他的奴隶身上一样”。
当家庭成为生产劳动的基本单位,女性便在家庭经济中退居于从属地位,这种父权制下的从属关系进一步禁锢了人们的思想,造就了社会对男性、女性对男性的盲目崇拜。
女性在不自觉中依赖甚至依附于男性而生存,而由此所造就的性别歧视的观念不只体现在职场上、生活里,更深入了大众思想。女性受到这种隐含性别歧视的观念影响,认为“女人很难成功”,所以只能通过依附于男人来实现社会资源的获得。于是,男性在社会中更容易被女性看作是实现自我提升的路径,而与之对应的将与自己争夺男性的其他女性则会被视为敌人。
(二)古代婚俗影响两性价值观
在古代,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婚姻模式是一夫一妻多妾制,“妾”在《现代汉语词典》 有“女奴”之意,是由周礼时代贵族嫁娶中女方陪嫁的同族女性亲属演变而来。可即便中国古代法律在婚制上对于一夫一妻的规定相当严格,严禁在同一时间内有两个“妻”,但是在现实的婚姻生活中却可以“一夫多妻”来概括。4
而在古代西方,基督教之前的古希腊、罗马时代,它们实行的实际上也是一夫一妻制。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圣奥古斯丁曾说,一夫一妻制是“古罗马以来的风俗”,是罗马文明对基督教文明的优秀贡献之一。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家庭的男主人与其女奴发生关系,也是不被禁止的,古罗马社会对这类关系的限制仅是从宗教和情感关系等方面不会危及现有家庭的完整性即可。
因此,我们可以说,“一夫多妻”的婚俗在中西方文化中都是存在的,而这样的婚俗实际上影响了社会对男女两性关系的认知。作为男性,在两性关系中往往是处于主动地位,且拥有较强灵活性和自由性。正如《诗经》的《国风·卫风·氓》一文中所提到的“士之耽兮,犹可脱也。女之耽兮,不可脱也”,女性在两性关系中则常常处于弱势和被动处境。
“一夫多妻”的婚俗在古代社会的长期存在影响了社会常规的两性关系观念,这种影响广泛而深远,直到今天还禁锢着我们的性别思维。
(三)社会资源分配的性别差异
在当今社会,受男女生理差异的影响,社会资源分配层面的性别差异正以一种较为隐性的方式存在于我们的生活当中,其中最明显的差异体现在就业上。
女性往往被认为不适合从事体力劳动与对身体消耗较大的职业,同时由于女性的生育角色,其在就业过程中也往往会受到不公平对待。尽管“男女就业平等”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是被广泛认可的理念,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出于利益最大化的经济考虑,女性在就业问题上相对于男性来说还是要面对更大的竞争压力。而针对女性生育所衍生出的大量问题,至今也很难有较为完善的制度保障。
在除就业以外的其他社会生活领域,这种资源分配上的不平衡同样存在,而资源分配的差异就自然而然地带来竞争。当女性长期处于一种竞争的状态中时,其就很难分辨何种竞争是正常且良性的,什么样的竞争又是无意义且恶劣的,这就使得许多女性身陷“雌竞”而不自知。
(四)互联网观点传播的特性
互联网作为一种全球性的开放的信息网络,提供了连接世界各地信息的便捷路径。
互联网摆脱了以往大众媒体信息传播存在门槛的局限性,使信息传播变得真正“大众化”,实现了大众传播与人际传播的有效兼容。数字化的信息传输方式使大众在社交媒体上表达观点变得更加迅速便捷,而全球化的特征更是打破了地域藩篱进而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信息多样性。
而基于这样的互联网特性,我们也不难发现受众在使用社交媒体时存在的一些难以避免的突出问题。一方面,用户信息的匿名性和互联网审查机制的缺失使得信息的内容产生了较大的差别,人们表达观点更加自由的同时也更加肆无忌惮。另一方面,由于信息的传输速度加快、受众的覆盖范围更大,在互联网讨论中极易出现个人观点的病毒式传播。
当大众处于一个信息密集的环境中时,辨别信息的能力就显得更加重要。观点的碰撞和传播并不一定产生的都是有益的想法,还可能是盲从和一个又一个“沉默的螺旋”。
当社交平台中的“雌竞”行为打破其原本的狭小空间而成为互联网语境中可以被模仿的“网络迷因”,我们很难绝对地说互联网在其中起到的仅仅是积极作用。
(五)社会发展阶段制约性别意识发展
社会的发展程度不足也是影响“雌竞”现象的重要因素之一,当整个社会处在高速发展和追求生产力的阶段时,人们就长期处在一种思维惯性当中,而很难有余裕思考性别问题。伴随着社会发展程度的进一步深化,人们在满足基本的温饱与物质层面的需求之后,才开始寻求观念层面的突破与进步。
性别问题与其他弱势群体的问题在某种程度上是相似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因为相对而言“不重要”、“不显著”、“不突出”而受到忽视,女性群体自身甚至是整个社会的自我意识还缺少发展也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雌竞”现象的出现。
四、我们应该如何看待“雌竞”现象?
近年来,“厌女症”的概念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我们的信息环境中,迈阿密大学教授Berit Brogaard曾对这一概念进行过通俗的阐释,认为其指“对全体女性或某一类型女性的憎恨。当女性为按照厌女症患者心中的女性标准思考或行事时,他们就会产生这种憎恨。”而不管是“雌竞”现象,还是互联网语境中出现的其他“厌女行为”,我们都应当充分地意识到,这并非是个体的缺陷和狭隘所带来的结果,而应当是整个社会文化影响下的产物,是父权社会的集体意识。
女性不愿接纳自身的生理性别,实际上是不愿接纳社会所给予女性的刻板印象。软弱、愚蠢并非先天就是女性独有的缺陷,只是社会规劝下的对女性的污名化。而摆脱这些恶意的有效方法并非是与自我的先天特征划清界限,也并非是否定和仇视其他同性,而是应当学会接纳自己,并自我认同。
当女性被社会教育“要视其他女性为敌”时,主动觉察厌女症不仅有助于我们客观批判地看待社会,还能帮助个体更好地面对现实、过好自己的生活。
我们的社会也应当真正达成一种“平等”的共识,而不是高喊着“男女平等”的口号却在实践中采取性别歧视的行动。这种平等需要从宏观到微观各个层面的践行,例如在两性关系中,双方都应当将对方看作平等独立的生命个体,女性应当更加注重培养自己的独立意识,男性也应当给予女性充分的尊重与独立空间。
互联网作为一种有极强传播力的大众媒介,应当为性别议题提供一个无差别的、可供充分讨论与表达的空间。同时,媒体也应当发挥大众媒介的引导功能,通过议程设置等方式引导大众关注、了解、探讨性别议题,培养公众形成正确的性别价值观。
在教育领域,国家应当有规划地逐步增加性别相关专业课程,引导孩子们从青少年时期就要树立正确的性别价值观念。从义务教育到高等教育、职业教育的各个阶段,在学校和家庭教育中,都应当强调正确的性别观念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作用。
结语
我们就生存在这样一个社会当中,性别造成的资源差异、固有的性别印象和传统的男权社会遗留观点压抑着我们每个人的思维方式。面对这些自觉或不自觉的厌女行为,我们应当将其放置到整个社会文化的语境中讨论,并在开放的讨论中寻找思想层面的更具有普适性的解决方法。推动性别平等的行动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这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参与和努力,我们都需要在探索的过程中不断成长,并且坚信总有一天会有所收获。
注释:
1、景欣悦.复义表达、话语策略与文化结构——“厌女”的三副面孔[J].中国图书评论,2021(05):16-27.
2、徐智,高山.网络女性自治区中的性别歧视内化——自媒体美妆视频中的女性嫌恶现象及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9,41(06):145-163.
3、[日]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M].王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4、陈筱芳.春秋以及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2):160-167+194.
参考文献:
[1]帕特里克·D·墨菲,王月.生态女性主义视角下的男权崇高匡谬[J].江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03):25-32.
[2]徐智,高山.网络女性自治区中的性别歧视内化——自媒体美妆视频中的女性嫌恶现象及批判[J].国际新闻界,2019,41(06):145-163.
[3]厌女文化污染着我们文明生存的土壤[N]. 沈睿.中国妇女报.2015 (B01)
[4]如何认识网络舆论中的暴力现象[N]. 彭兰.中国社会科学报.2009 (006)
[5]李丹.从木子美到小月月:社会厌女症的网络表达探析[J].东南传播,2011(08):64-65.
[6]自由的困境:社交媒体与性别暴力[J]. 黄雅兰,陈昌凤.新闻界.2013(24)
[7]景欣悦.复义表达、话语策略与文化结构——“厌女”的三副面孔[J].中国图书评论,2021(05):16-27.
[8]胡宏超.互联网语境下女性媒介话语权的缺失与提升[J].青年记者,2016(23):9-10.
[9]雷跃捷,金梦玉,吴风.互联网媒体的概念、传播特性、现状及其发展前景[J].现代传播-北京广播学院学报,2001(01):97-101.
[10戴雪红.《第二性》与“厌女症”[J].粤海风,2009(01):63-64.
[11]王宏维. “厌女症”的文化批判[N]. 南方日报,2005-01-27(A07).
[12]陈筱芳.春秋以及中国古代的一夫多妻制[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02):160-167+194.
[13][日]上野千鹤子.厌女:日本的女性嫌恶[M].王兰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5.
[14]王晓丹.告别厌女———在情感与关系中琢磨自我[A].王晓丹.这是爱女,也是厌女[C].新北:大家/远足文化,2019:11.
[15][法]西蒙娜·德·波伏瓦.第二性Ⅰ[M].郑克鲁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19.
[16][英]约翰·斯图尔特·穆勒.妇女的屈从地位[M].汪溪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5:26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