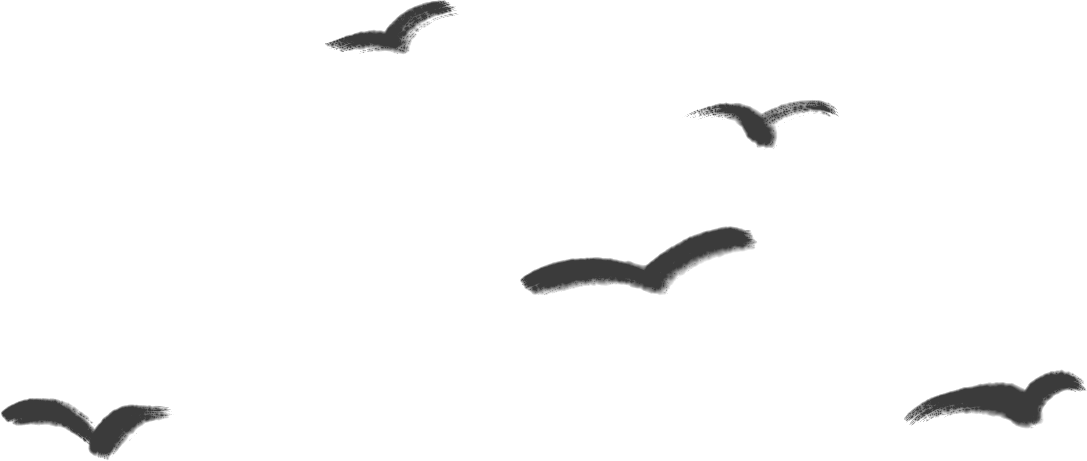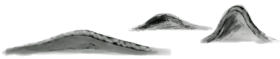
讲
座
回
顾
2024 年 11 月 6 日 18:30~20:30,在中传学术中心 V01 报告厅,“中国通史”系列讲座第四讲顺利开讲。讲座专题为“魏晋南北朝”,由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叶炜老师主讲,中国传媒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王宇英老师主持。

魏晋南北朝时期最大的特点就是“分裂”,分裂和动荡从 189 年董卓之乱开始,到 589年隋灭陈结束,跨越 400 年。叶炜老师以“分裂”为关键词,将此次讲座划分为四个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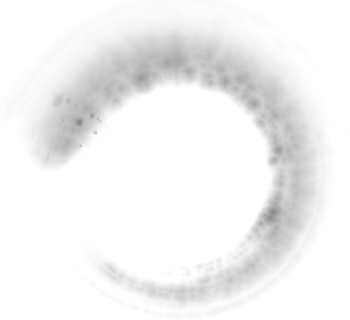
第一部分“从统一到分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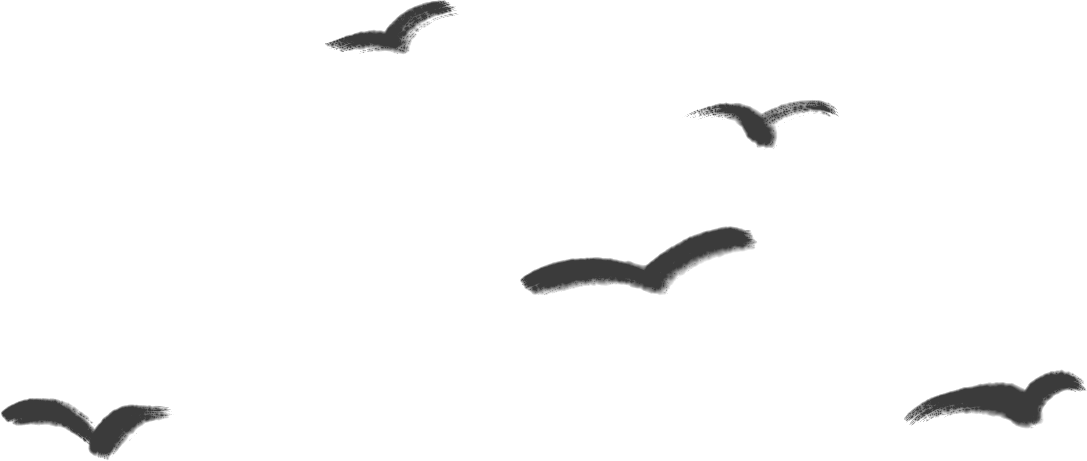
该部分主要介绍东汉末年和西晋的两次分裂。首先,叶炜老师从三个方面分析东汉瓦解的原因:全国人力资源的流失、全国财税资源的减少、最高法权的旁落,这是东汉中央集权衰落的表现。
从东汉到三国,国家掌控的人口数量下降约80%。其原因包括自然灾害的影响,但自然灾害的破坏力不至于此,根本原因还是东汉以来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发展,地方豪强掌握了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控制权,占据土地并使大量户口沦为私家佃客。
由此,中央失去了对土地和人口资源的控制力,而豪强地主的势力壮大,逐渐掌握地方实权。另外,汉末州刺史改成州牧、监察区变成行政区、二级制变三级制,导致地方官员的权力增加,最终诱发割据之战。三国纷争结束后,司马氏的西晋政权实现统一。

然而,西晋政权的统一局势十分短暂,很快发生了“八王之乱”,进而导致“永嘉南渡”。
对于西晋快速分裂灭亡的原因,叶炜老师进行了三点总结:统治集团严重奢侈腐化、宗王权重、族群内迁引发的族群矛盾。首先,统治集团生活骄奢淫逸,衣食住行皆奢侈铺张,甚至皇帝与大臣之间常常炫耀攀比。制度严重腐败,买官卖官现象屡见不鲜。
其次,中央封宗室27 王,让宗王担任都督,手握军事大权。此举本意在于让宗室巩固皇权,却诱发了宗王之间权力斗争,导致“八王之乱”。
最后,寒冷的气候迫使北方游牧族群发生迁移,一部分南迁进入传统华夏地区,主要包括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少数族。这一时期的族群交往程度有所加深,然而,“八王之乱”时期,各王都希望少数族加入自身势力,因而激化了族群矛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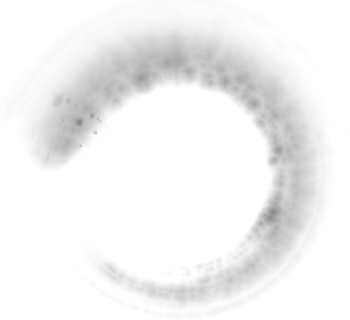
第二部分“东晋南朝皇权的变态与回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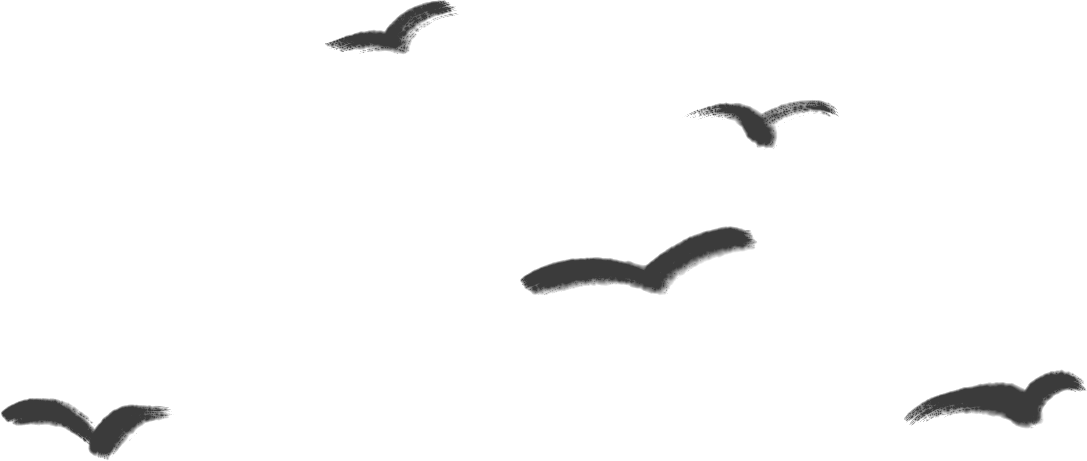
南朝时期的总体变化有四点,首先,魏晋时期,中国大体呈现“南强北弱”的局面,而此后南朝整体实力不如北朝,呈“北强南弱”;
第二,门阀士族势力发展壮大,至东晋成为门阀政治的时代,至南朝向皇权政治回归;
第三,自东晋至南朝末,皇帝的身份从高级士族变成低级士族,最后变成寒人出身;与之相应,东晋时期朝廷主要以士族当权,而南朝时期寒人兴起掌权。

在第二部分中,叶炜老师重点讲解了“门阀政治”的概念。“门阀”一词原指门前记述功状的柱子,左为“阀”,右为“阅”。自东汉起,它由记述个人功劳演变为家族荣誉和地位的象征。
叶炜老师推荐了田余庆先生的《东晋门阀政治》,并引用书中观点介绍门阀政治的概念:门阀政治是士族与皇权的共治,是皇权政治的变态,它来自皇权政治,又逐步回归于皇权政治。严格意义上的门阀政治只存在于东晋。在其他时代,士族也不同程度地起作用,但都算不上门阀政治时期。
“王与马,共天下”,体现了东晋琅琊王氏兄弟与司马氏皇权的共治,反映了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也开启了东晋门阀政治的格局。门阀制度最大的表现是按门第选拔和任用官吏,士族免徭役、婚姻轮门第,都是从士族选官制度衍生出来的。门阀政治强大到“士大夫故非天子所命”,皇帝无法干涉社会等级划分。
东晋门阀内部骄奢腐败严重,逐渐腐蚀高级士族自身,于是,到南朝时期,高级士族没落,低级士族兴起。为了巩固皇权,统治阶层内用寒人、外托宗室。门阀政治的时代自此落下帷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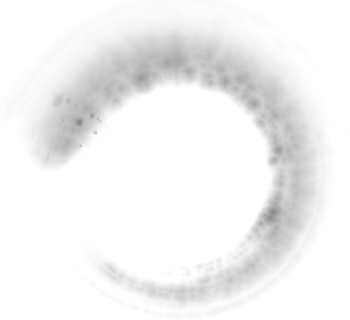
第三部分“十六国的胡化与汉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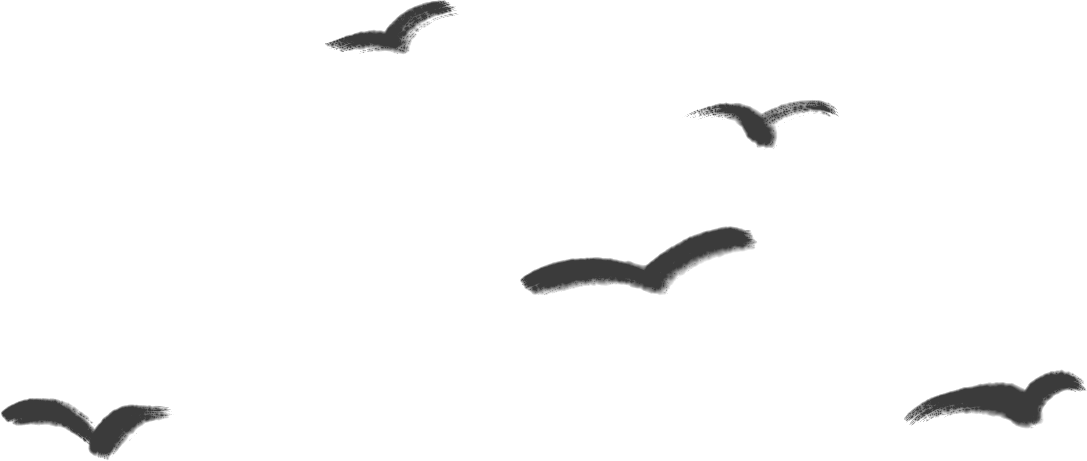
叶炜老师在这一部分讲解了北魏的汉化和六镇的胡化,并指出,汉化是北魏孝文帝赐汉姓的目的,但胡化不是西魏复、赐胡姓的目的。
一,复、赐胡姓,出于政治目的,目的只在工具层面,不在价值层面;二,赐鲜卑姓同时也常赐汉名,而且都是汉字雅名;三,宇文泰还还模仿《周礼》,建立六官制度。

十六国和北魏前期总体特点在于胡汉杂糅、胡汉分治。北魏汉化的措施诸如:将东晋南宋齐、十六国定为僭伪,声称北魏继承西晋之金德为水德,证明自身合法性;迁都洛阳;皇帝按姓氏划分社会等级,定姓族、改汉姓;禁止鲜卑服饰、鲜卑语言;规定鲜卑贵族死后不得归葬。
北魏汉化的措施促进了胡汉族群凝聚,却也是对自身鲜卑文化的否定。六镇之乱导致了北魏的瓦解,东魏西魏、北齐北周又出现了胡化现象。具体表现例如统治阶层复、赐胡姓。
叶炜老师引阎步克先生在《波峰与波谷》中的见解,说明汉化与胡化对于帝国统一的意义:“交替的‘胡化’和‘汉化’孕育出了强劲的官僚制化运动,它扭转了魏晋以来的帝国颓势,并构成了走出门阀士族政治、通向重振的隋唐大帝国的历史出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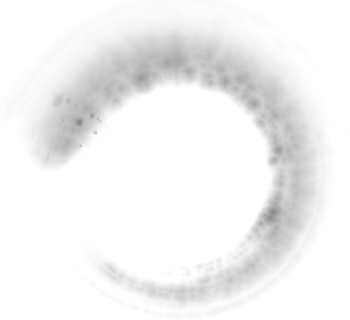
第四部分“分裂时代的历史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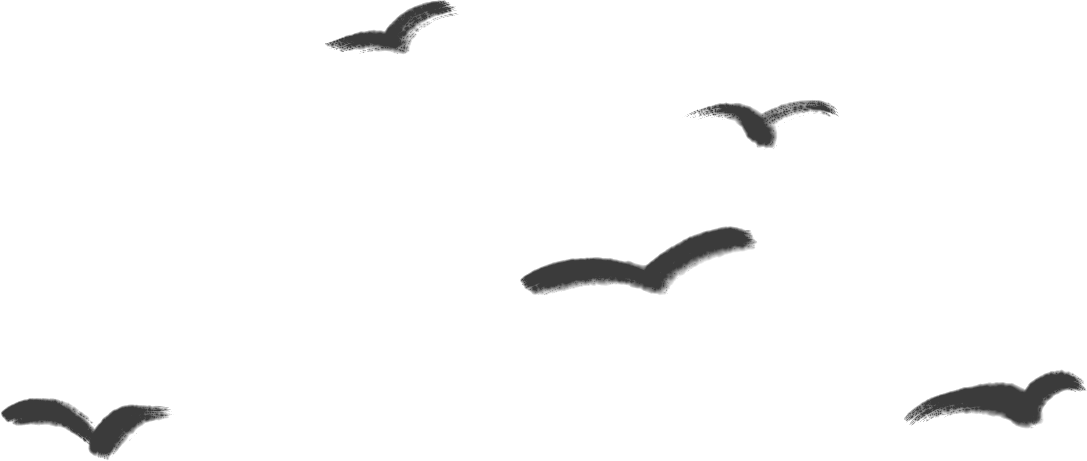
为什么中国经历了 400年的分裂还能重归统一?
这一问题引起了中外学者的重视,对外国学者尤其具有冲击性。目前仍然没有很完美的回答,叶炜老师介绍了一些国内学者的看法。田余庆先生认为中国历史拥有统一的传统,该传统源自秦汉。姚大力先生进而指出,回归统一主要依赖正统性,也就是合法性的力量,秦汉时期建立的政治制度模板对后世影响深远。

历史遗产问题具体可分为三类:国土开发、文化整合、族群凝聚。
首先是国土开发问题。战国时期,南方土地开发利用程度远低于北方,在《尚书·禹贡》篇中属于下等。秦汉时期,南方得到开发,魏晋南北朝时,南方土地更是加快发展。另外,参照田余庆先生的观点:中央集权国家,辉煌的文治武功,灿然可观的典章制度,规模巨大的建设工程,尽管多出现于统一时期,但是地区的经济、文化的发展,包括小工程的兴建,却往往在分裂时期更为显著。
一般说来,统一王朝的政治、文化以至经济中心多在首都及少数重镇,只有这些地方才有优先发展的机会;远离交通干线的地区,例如南方腹地广大地区,发展速度则要缓慢一些。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现象,往往在交替出现的分裂时期逐渐得到一些弥补。再有是文化整合与族群凝聚问题。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族到唐代以后进入华夏的族群。
因此,如费孝通先生所言,汉族的壮大并不是单纯人口的自然增长,更重要的是靠吸收进入农业地区的非汉人。从这个角度说,汉族是“炎黄子孙”是一个不准确的说法,“炎黄子孙”只是很狭窄的一系。文化的整合就是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隋唐文化繁荣的基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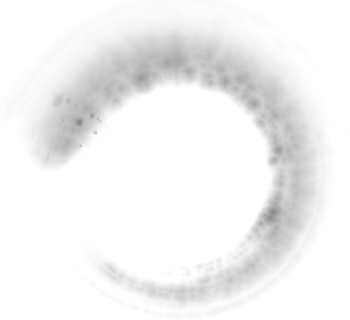
提问环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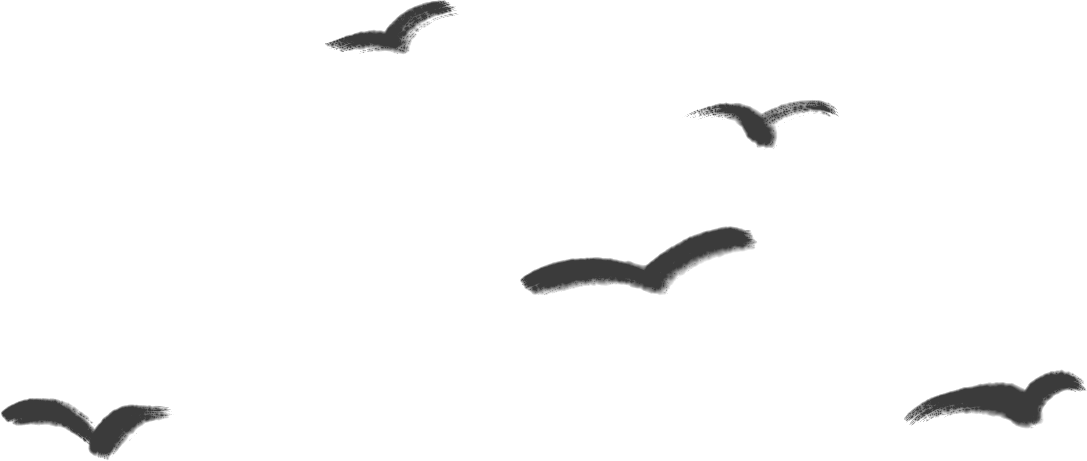
Q:叶炜老师,我想请教三个问题。
第一,我看了您的文章《从表、状分化看唐人文集中“状”文体的生成》,注意到其中文史兼治的观念。我又搜了一下,发现 22 年您在厦大做过一次“唐人文集中的制度史”的讲座,里面也提到了作为公文“状”的问题。请问您作为历史学者,如何看待集部文献?
第二,您最初的兴趣点在于隋唐史,请问打通了魏晋南北朝历史对您的研究有什么帮助?
第三,您作为《唐研究》的主编,能否分享一些唐代史学研究的学术热点?

A:第一个问题,我关注集部史料,源于陈寅恪先生说研究隋唐最重要的两部文献是《资治通鉴》和《全唐文》。集部文献当然有其独特价值。关于我写“状”那篇文章的思路,是由于我有这样一个思考:我们现在阅读的唐人文集,不是唐人文集的原貌,而是散佚后宋人甚至是更晚的学者编纂的。我的思路是争取能获得一些对唐人文集原貌的认识,从唐人文集中“状”的情况来考察“状”作为文体被接受的过程。
第二个问题,《唐研究》现在一部分是专栏,一部分是投稿文章。希望专栏能够反映唐史研究中的从材料到方法的一些热点。现在正在编辑的是请南开大学夏炎老师主持策划,利用唐代石刻的一组研究。希望推动利用石刻对唐史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下一卷请清华大学方诚峰老师主持和策划,围绕唐宋皇权等问题做讨论。
第三个问题,魏晋南北朝与隋唐历史打通的益处在于可以更广阔的角度看问题。研究魏晋南北朝史,向来有打通的传统,或秦汉魏晋南北朝,或魏晋南北朝隋唐,阎步克老师的视野就很开阔,从先秦到隋唐都能做深入的研究,对宋元明清也都有思考。我也是向阎老师等前辈学者学习吧,尽量地关注得多一点,对自己的思考有些促进。
Q:隋唐与汉末士族的产生路径有所不同。请问士族的概念该如何界定?我听闻其他学者说五代、三代为士族,但也有别的说法,究竟什么才是士族?

A:东汉士族的产生,有的是靠地主起家,有的是靠当官等等。但士族作为一个现象,总体来说是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三位一体的。
如余英时先生所论东汉士族,一方面是强宗大姓的士族化,另一方面是士人在政治上得势后,再转而扩张家族的财势。具有比较鲜明的文化色彩,是东汉至魏晋南北朝士族的通常形态。